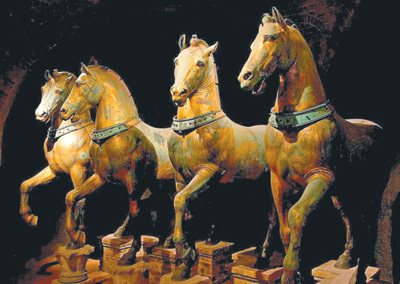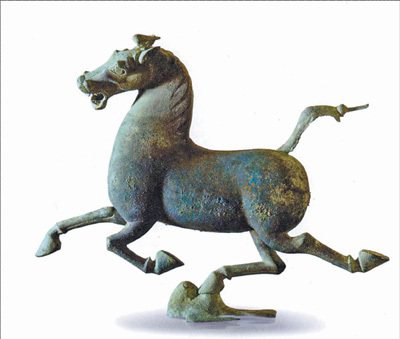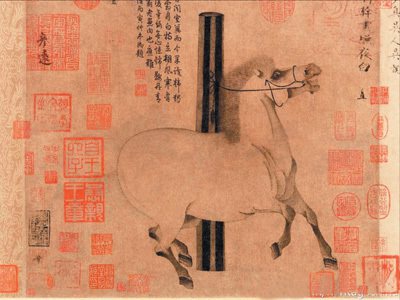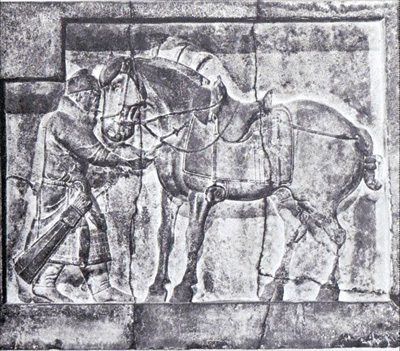勤勞於農作的阿河 趁著他的農地在進入深度睡眠之前
挑了一個冬陽暖照的好時光 邀約同學一起來焢窯
對於這個「一起」同學們是有一點兒心虛 嘛有無限ㄟ感動

因為從挖土 曬土 推疊土塊搭窯 搬運燃料 燒柴升火 全都是阿河的個人秀
說要幫忙的阿村跟阿明 嘸知到底是ㄉ一兜位咧~~~~~~~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燒了好久的火 終於把土塊燒紅了 阿河的臉龐已被火氣燻烘得比關老爺子的雙頰還紅哩

俗話說「主將無能累倒三軍」 我們是同學攏剩一只嘴 而把阿河操到累歪歪
幸好有阿珍 阿美 阿鳳伊ㄟ尪這幾位最佳人夫 下田輪流當「爐主」 感恩啦


當土窯被燒成熾紅之後 阿登他們把阿明 阿美和阿河夫人等採買來
經由阿美 麗 妙 香 珍 滿 鳳 碧 邁 網 霞 霜 姿 珠們
分工清洗並用錫箔紙 濕報紙捲包以及置入牛奶罐裡的豐富食材
如玉米 菇菌 蔬菜 蕃薯 芋頭 馬鈴薯 雞肉 雞蛋等往窯坑裡塞放
然後把高溫的土窯整個打掉 用力將土塊敲碎 完整的覆蓋住食材 將它們慢慢悶熟
看阿嚴 阿河 阿輝這一畫面 突然唱起了「守著陽光守著泥.........」
※泥中那些令人垂涎的美食
此刻的空氣中飄浮瀰漫著的正是我們難以忘懷的味道


在故鄉美麗的田野裡嬉耍 焢土窯是多數同學共有的記憶
為了敘舊 為了重溫焢窯之趣味 許多同學從北中南各地專程回到大雅